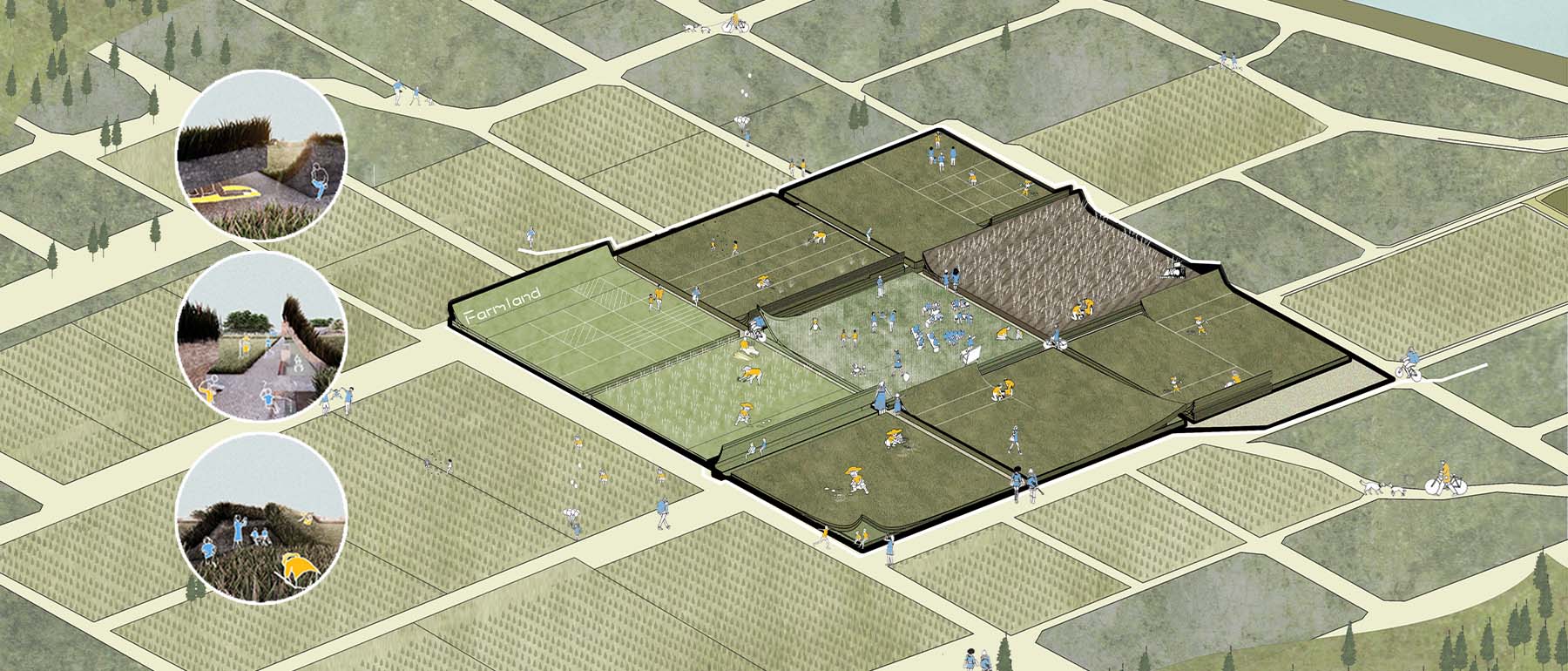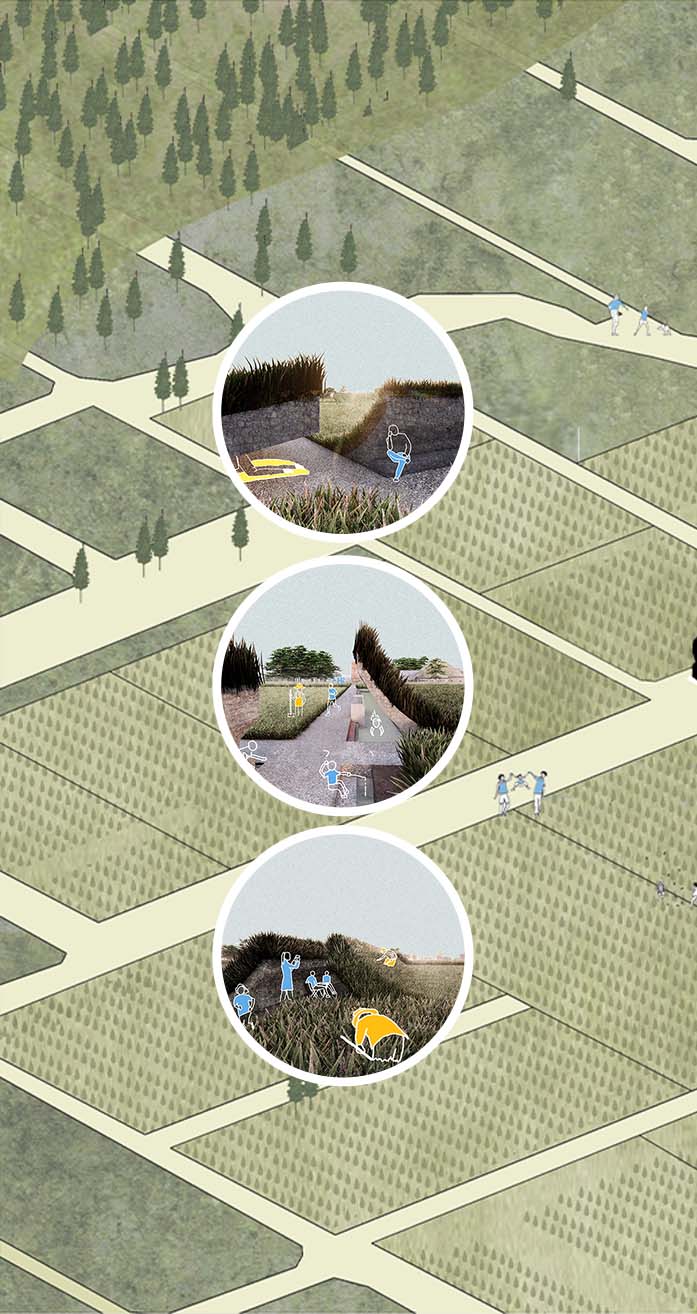Latest works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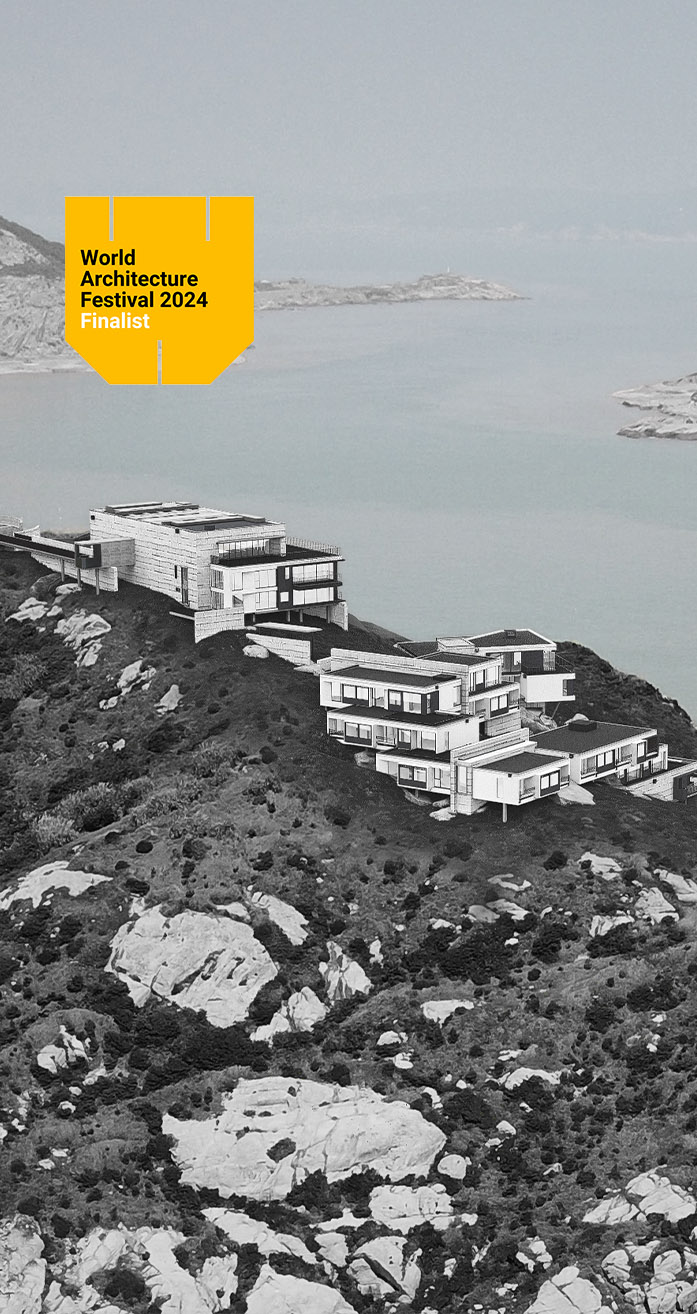
Huanglong Island Hotel was shortlisted for WAF 2024


Boatyard Hotel won the Winner in 2024 Hospitality Design (HD) Aw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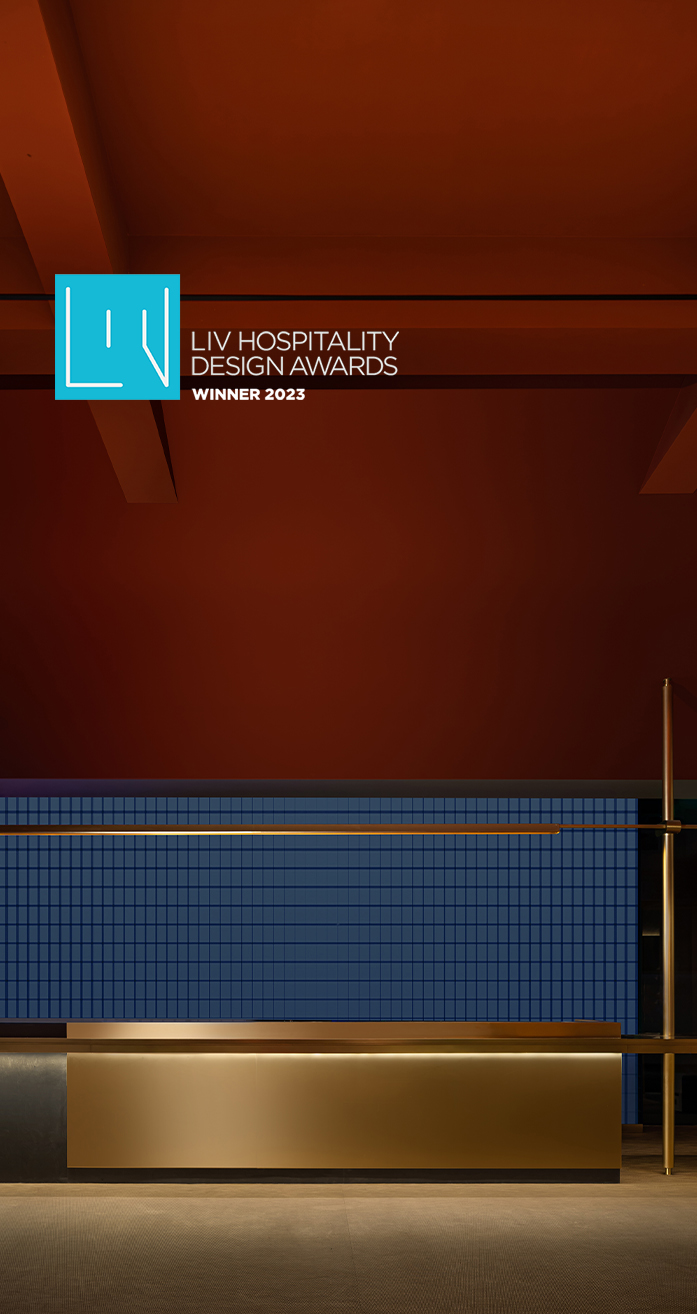
Ansan Hotel and Boatyard Hotel both won the Winner of LIV Hospitality Design Awards


WJ STUDIO's Boatyard Hotel Won Highly Commended at INSIDE World Festival of Interiors


Mr. Hu Zhile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the Andrew Martin International Interior Design Summit
©COPYRIGHT2024【万境设计】 版权所有 浙ICP备16042009号-2